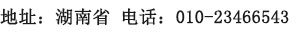陈振宇按
法院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但不能替代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决定了法院监督行政职权行使的边界。《行诉解释》增加的五类不可诉行为,不是新设,而是对以往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明确。本文作者对涉相关不可诉行为的既往司法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就具体适用过程中的注意点作了精准分析。阅读该文定会使我们加深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新规定的认识和理解。
《行诉解释》的精读(四)
——哪些行为不可诉?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叶一
年2月6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这部全面的司法解释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值得逐条精读研学。新司法解释开篇于“受案范围”,受案范围是决定当事人能否将争议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首要条件,划定了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边界,具有“头道门槛”和“总阀门”的作用。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司法解释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对当事人依法正确主张合法权益,以及人民法院保障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的实效,意义重大。鉴于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针对受案范围作出具体规定,让我们来看看,新司法解释与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相比,在受案范围方面的规定有哪些不同。
从立法技术上看,新旧两部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都采取了“正面概括+除外列举+法律注释”的行文结构和表述方式。从条文内容的对比来看,两者的差异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新司法解释对《执行解释》原有条文个别文字的调整,与《执行解释》的规定并没有实质区别。如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将《执行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调整为“行政机关”;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将《执行解释》中的“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调整为“行政指导行为”;针对“国家行为”的第二条第一款,删去了《执行解释》第二条中的“实施戒严和总动员”;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第二条第二款,将《执行解释》第三条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为“规范性文件”。上述这些文字的调整,笔者个人理解,有的是依据宪法法律调整作出的相应变动,有的是为了保持与《行政诉讼法》表述的统一,有的是文字精练的需要,在具体适用中应该不会产生大的问题,在此不作赘述。
另一类是最高法院在总结过去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成熟经验基础上,通过新司法解释新明确的内容。比较醒目的是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至第(九)项的条文,它们增加规定了五种不可诉的行为。结合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长在新司法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和说明,对照相关司法解释、最高法院批复、典型案例裁判要旨,笔者逐一浅析个人学习心得:
一、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可诉
江必新副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对外性是可诉的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内部所作的行为,例如行政机关的内部沟通、会签意见、内部报批等行为,并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因此不属于可诉的行为。”这是正向解读这条规定,如果倒过来理解,意味着“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可诉”。这就引出了“内部行政行为外化为可诉的行政行为”的观点。据笔者观察,该观点肇始于年《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刊载的“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陕西省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生产责任事故批复案”(以下简称“宏盛公司诉延安安监局批复案”)。年,在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五批指导性案例中,“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指导案例第22号)再次肯定了这一意见。为何在新司法解释中未采用“内部行政行为”的表述,笔者揣测,在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中,内部行政行为有其特定含义,指的是行政机关对本系统、本机关的人事、财务等方面的管理行为,基本对应《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所称的“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也许是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新司法解释用了“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表述。
正确理解这条规定,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产生外部法律效力”这部分内容,核心在于“外化”。“外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因被诉行政行为(如会议纪要、批复等)是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产物而必然脱离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而要看它在实际上有无通过一定途径对外,对行政程序外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产生影响。从以往司法实践中认定可诉的外化内部行政行为来看,其外化应当是指行政机关依职权外化,通常表现为两种途径:一种是行政机关的主动告知。在“宏盛公司诉延安安监局批复案”中,延安市安监局代表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对《子长县“10.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责任的认定,未正式送达宏盛公司。作为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之一的子长县监察局将批复作为谈话内容告知宏盛公司,并送达了复印件,从而使批复外化。另一种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即行政机关直接依据会议纪要、上级批复等内部文件或决定对相对人实施执行行为,从而使效力外化。在“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中,来安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的批复,来安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制作并送达对外发生效力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即直接交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根据该批复实施拆迁补偿安置,产生了外化的效果。
如果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并非行政机关依职权而为,是否使内部行政行为转化为可诉的行政行为?在“宏盛公司诉延安安监局批复案”的案例分析中强调,之所以强调依职权外化,主要是区别于一些相对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如私下打听、索取甚至窃取一些内部文件,一旦发现其中对己不利,即行起诉,此时,尚无法证明这些内部行政行为必将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而不应将其列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过程性行为不可诉
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将此表述为“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江副院长在讲话中指出,“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上述这些行为“尚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可诉。实践中,行政机关在作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之前,一般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果存在后续的行政处理、行政决定等法律行为,则后续的行为才是真正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通过起诉后续的法律行为,实现司法救济。新司法解释列举的情形都是比较典型的过程性行为,同时几乎都带有内部性的特点,笔者个人认为归入“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也没有问题。
新司法解释在列举后用“等”字收尾,这里的“等”应该是非完全列举的“等外等”。在实践中,还有受理、告知补正、听证等需要告知相对人或相对人参与的行政行为。从行政处理流程看,它们相对于最终的处理决定是中间性、阶段性的行为,因而可以归入过程性行为的范畴,这类行为是否因此就不可诉了呢?从最高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和相关案例看,应该并不尽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就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导致许可程序对上述主体事实上终止的除外。”因此,从可诉性的角度去判断某行为是否为过程性行为,不应从应然的、概念化的角度去认识,而要着重